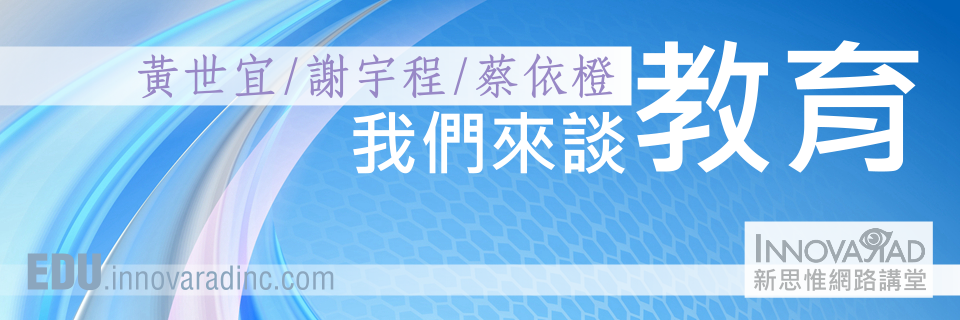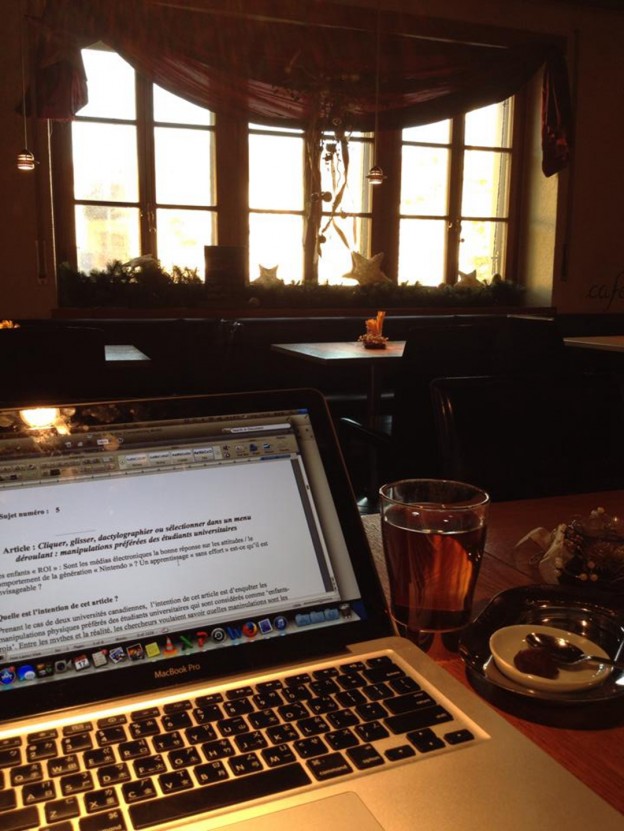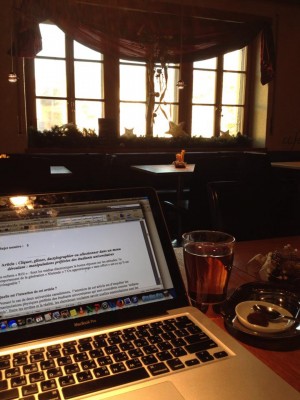講者:黃世宜 老師

Simone de Beauvoir……看到這名字,不禁讓我陷入回憶之中。她,是我大二時的精神偶像。
記得那一年,師範體系的學業很穩定進行著,未來的軌道似乎也已經看得很清楚:當老師,嫁人。當時親友所關心的,有沒有男朋友?是不是該找一個了?這個怎麼樣?要不要介紹聯誼?我突然為這一切的安排感到恐懼,於是在那一年,我迷上了西蒙波娃,原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法國,跟台灣這麼相似,壓抑、沈悶,尤其對女性。
因為崇拜波娃,我把她的作品傳記反覆咀嚼還不滿足,竟然開始動起腦筋,想讀懂原文資料追星。因此那一年暑假,我一邊打工,一邊把賺得的錢拿去請一對一的法文家教(那年代台灣沒幾個地方可以學法文),就從最基本發音讀起。
還記得老師是一個五官俊美,眼神深邃的法國紳士,優雅斯文。第一天上課,他很有禮貌地帶著濃濃口音的法式英文,告訴我他快要跟台灣未婚妻結婚了,然後,他問我怎麼會想學法文?因為他說他基本上都只能在台灣教英文賺錢這樣。我就很快跟他說,因為我喜歡西蒙波娃!
結果這個迷人的法國紳士整個呆掉,張大眼睛瞪著我。
然後接著拼命搖頭一直說,太可怕了!!你怎麼可以把這個女人當做偶像呢?你啊!少讀西蒙波娃,應該多讀讀雨果的作品!!
我那時突然覺得我好像說到什麼魔鬼的名字一樣,愣在那裡不知道怎麼辦,一直到幾年後,真的到了法國,在歐洲大學裡讀了存在主義還有雨果的作品,才突然瞭解當年那位法國男士的驚嚇。
不過,很有趣,一直把西蒙波娃當做偶像的我,到了歐洲,崇拜的情結反而漸漸淡掉了,我終於理解到,一個真正西蒙波娃的粉絲,是不會把西蒙波娃當做偶像的:因為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女人,她只把自己當成偶像,不斷超越自己,並為突破自己為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