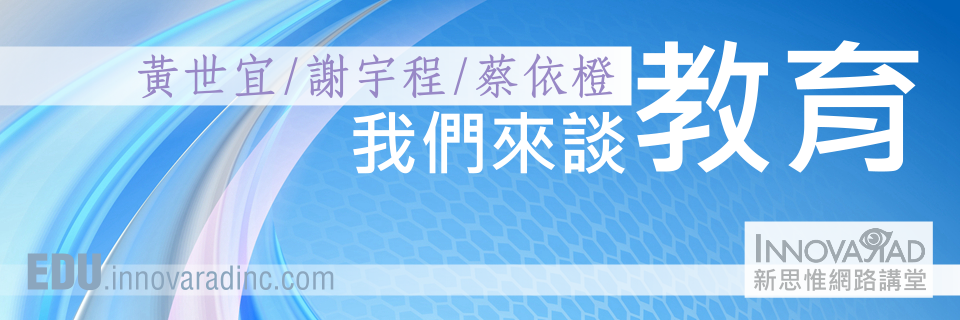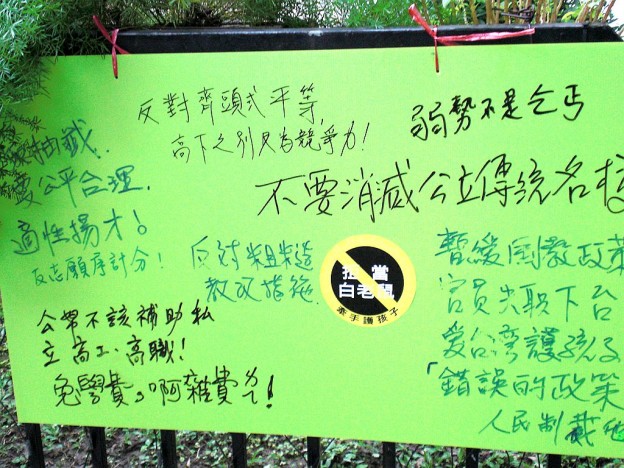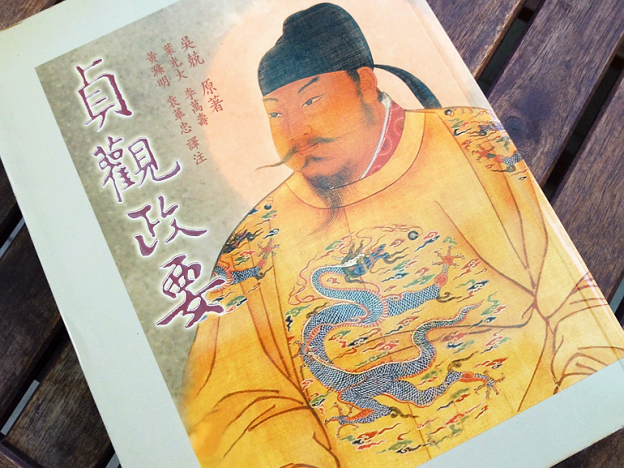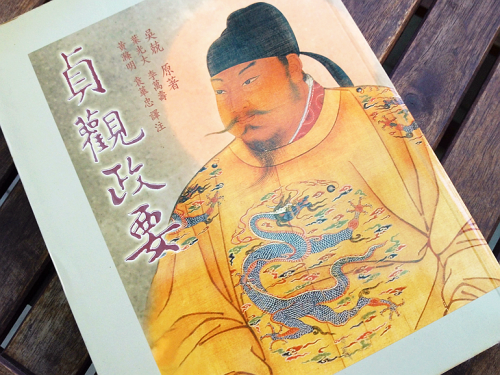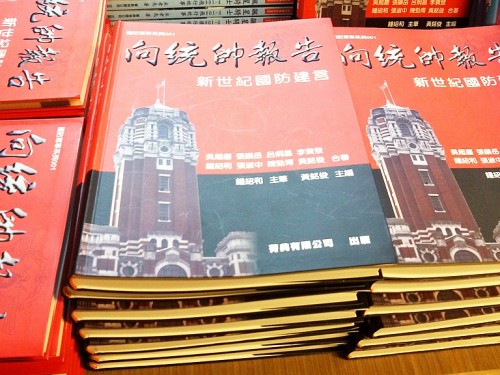講者:謝宇程 研究員
《重新衡量「學校教育」的效益和風險》這篇文章之中提到一個現象:上課不見得總是有利於教育,有時其實造成反效果。
面對這個社會上極多的學生無法有效學習,對學習沒興趣,厭惡和反抗學習,大多數人仍然認為錯在學生,他們智力低落,或者品性惡劣。但有沒有可能,是教育的模式有問題?有沒有可能,某些學校、某些老師,他們正在提供劣質的教育,而我們一直沒有看清?
四十年前,我們也不知道回收油、塑化劑、多糖重鹽、不用芭樂製造的芭樂汁有什麼不好,健康出問題只能怪自己衰。現在,我們知道哪些飲食方式會導致身體的病變。
今天,我們有沒有學著判別,也有品質不夠好的教育,可能造成孩子人生發展上的病變?這篇文章,我們來談談現今教育體系中會看到的三種品質。

孩子在學校中的成績不好,是他們的錯,或是教育體系失靈?圖為某次教改團體集會中的訴求告示。
最低品質:懲處威脅,硬塞強灌
最差的教育,是忽略學生的主觀意志和感受,基於各種規定,將學生像器物一樣看待,把他們集中在一個地方加以「製造」,而且不吝施以強迫。上什麼課,什麼時候上,用什麼速度來上,用什麼方式來上,都不顧及個別學生的差異和感受,反抗就受懲罰,有意見就是叛逆,學不好就是低劣。
這種教學之下,除了那些最順從的學生還能適應,會造成大量的學生憎恨學習,或對智識成長毫無欲求。這樣的課程模式,傷害的學生可能比助益的學生還多。
中等品質:放牛吃草,結果自負
稍微好一點點的教育,可能看似道家風格。也許是老師偷懶,也許是失去教學熱忱,也許他志不在此,總之,他不勤於提供材料,不認真上課,不認識學生,遲到早退,讀課本畫重點,不規劃安排…。
這樣的課程本身價值不高,但不是最差的,至少沒有積極地造成什麼傷害。有點興趣、有點上進心的學生透過別的管道自己想辦法學;沒有興趣的學生做別的事,自已找樂子,也許日後有一天他興趣開啟,會重新學習這個學問。

以嚴管勤教來說,許多補習班的老師反而是好老師,因為他們有財務誘因這麼做。圖為南陽街補習班的招牌。
高等品質:諄諄勸導,認真勤教
有一類老師,認真準備教材,課前仔細規劃,幫學生找好補充資料,想好笑話避免學生睡著,編好口訣讓學生易背。
他們認真教學生解題,告訴學生什麼是段考、升學考容易考的。他們認真的告訴學生,閱卷老師希望看到計算題怎麼寫,他們把怎麼樣的作文打高分。
對於不認真的學生,他們課後約談勸說;對於跟不上的學生,他們提供個別指導;對於考高分、拿獎的學生,他們自掏腰包買禮物。
這樣的老師夠好了嗎?不,在這個時代,面對真實的人生現場,我認為需要比原有的最好模式更好的教育和老師。
(繼續閱讀:未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學校教育和教師?)